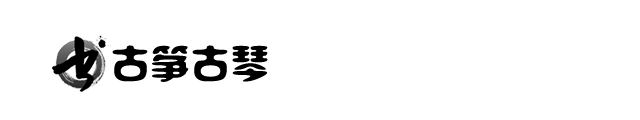摘要:古筝,这种古老的弹拨乐器,在今天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门艺术,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古筝与诗歌、书法、地方文化等传统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因其悠久的历史而常常被人们称为“古筝”。古筝的发明者和具体命名者目前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大家普遍都认同古筝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就已广为流传,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经过历代众多名家的努力传承,这一古老乐器不但没有丝毫的老迈之态,而是越发地富有青春活力。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古筝在乐曲创作题材的丰富、演奏技法的多样、教学方法的系统规范、乐器制作工艺的精湛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音乐启蒙到专业教育,从大众娱乐到高雅艺术,都有古筝的身影。
众所周知,音乐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古筝作为中国民乐的代表之一,自产生以来就深植于文化之中,它既能反映出一个时期、一个年代的文化潮流;还能充分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有时还能反映出一个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精神风貌。当然,古筝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地域性。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古筝从业者,就必须做到如古筝大师曹正先生所说的那样——“筝文合一,必成大器”。
筝盛于唐而源于秦,历代名家诗人都与筝结缘。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道:“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魏晋时期,“相和歌”中就有八种律奏乐器,曹丕、曹植这对诗人兄弟都弹得一手好筝。到了唐代,一些著名诗人为古筝写了许多流传至今的美妙佳句,反映了古筝在当时的盛行。李白《春日行》:“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筝。春风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升天行。”白居易的《听夜筝有感》:“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北宋著名词人苏轼多才多艺,他的《甘露寺弹筝》不仅是诗,更是抒发他自己弹筝的感受。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庭”罪遭贬谪后,曾去在今江苏省镇江市的甘露寺游览,并在寺北的多景楼里弹筝抒情,还写下了这首诗:“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唤取吾家双凤槽,遣作三峡孤猿号。与君合奏芳春调,啄木飞来霜树杪。”声声哀筝,倾诉了苏东坡的满腹怨愁;阵阵清音,感动了水中的女神和空中的白浪。但是,逆境却改变不了诗人豪放的性格,他没有沉湎于哀怨中,而是请夫人弹琵琶,与她合奏充满希望的《芳春调》。正因为苏东坡会弹筝,所以,他在一些诗词中对筝的描写和借筝喻意不落俗套。在《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一词:“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诗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由此可见,苏东坡作为北宋的古筝名家也一定当之无愧。
发展至些,古筝已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演奏乐器,而成为了一种被文人骚客抒发心意、借以言志的对象和载体。可以说,古筝从此与诗歌(词)的结合越发紧密,相互影响,直到今天。
书法是我国艺术宝库中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一门独特的艺术。中国自古就有“琴、棋、书、画”,是文人骚客(包括一些名门闺秀)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书法与音乐是姐妹艺术,这是因为书法具有音乐的刚柔美、节奏美、情感美,所以书法艺术也被人们称为“无声的音乐,纸上的五线谱”。书法由于它的色彩极为简单而且反差极大:黑色的墨和白色的纸,因此书法必须依靠线条千变万化,才能获得艺术的魅力。一幅好的书法必须具备线条的轻重、长短、干湿的变化,使态体布白合乎韵律,即有美的旋律,使点线达到矛盾的对立统一。这也就有了音乐的节奏感,有了音符的高中低,有了旋律的轻重缓急。线条的粗重、湿润有如古筝低音的铿锵之美,恰似黄河奔腾,有一种无形的外力推促您,使人感到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反之,线条的轻细,有如古筝中音的柔和之美,有高山流水、渔舟唱晚、涓涓流淌的感觉。线条的长短,就如音符节拍,时而急促有力,时而迅缓细流,使节奏感更为明显。对此徐悲鸿先生有如此评价:“一幅好的书法,节奏感要强,宛如音乐之美,金石铿锵之硬也。”书法和古筝音乐在表现人的感情时有异曲同工之妙和殊途同归之感。当书者遇到喜事时,喜悦心情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纸上,此时,用笔急速,似“丰收锣鼓”、“幸福渠水”,如古筝高音的轻巧欢快;当书者悠哉悠哉时,写出来的字就会线条弯曲柔长、章法错落有致,犹如“小桥流水人家”,让人轻快舒适,宛若洞庭湖水之美。当书者哀愁、思念时,忧伤伴随喜怒哀乐的回忆心情,如“秦桑之曲”、“汉宫秋月”,写出来的字便笔画如泪。总之,古筝和书法有相通之处,运笔的从容与激烈表现出来的节奏感不同,这一点在古筝音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欣赏古筝音乐和欣赏书法作品都可以从中体会到人的内心感受、人的情绪和思想。这就是书法与古筝音乐的关系。
青年古筝演奏家罗小慈在“筝·乐·诗《陆游与唐婉》”中,创造性地将古筝演奏、现场书法、诗词吟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开创了中国民乐界的先河。
自秦、汉以来,古筝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流派。
陕西筝:陕西地区是中国筝的发源地,这里有丰富多采的戏曲和民间音乐,是近年来复兴起来的流派。代表作品有:《秦桑曲》、《姜女泪》、《香山射鼓》、《绣金匾》等。它的乐曲有的来源于陕西榆林流传下来的小曲;有的是根据西安鼓乐古谱编订的乐曲;还有很大一部分乐曲是根据秦腔、眉户改编创作的现代作品。陕西筝曲涉及的戏种、乐种繁多复杂,既有秦腔音乐那大起大落、激昂慷慨“英雄曲”之悲壮气势,又有眉户、碗碗腔音乐那如泣如诉、细雨缠绵、委婉酸楚的“凄凉调”。首先是音律上的特殊性和二个变音的游移性。七声音阶中的四级音偏高,七级音偏低。其次,在旋律进行上,一般是上行跳进,下行级进的。第三,在弹奏时左手按弦,使用大指较多,这是出于旋律进行需要而必然使用的技术。第四,风格细腻,委婉中多悲怨;慷慨急楚,激越中有抒情。
河南筝:由秦筝传入河南和当地民间音乐(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充分融合发展,成为后世有名的中州古调。代表作品有:《山坡羊》、《打雁》、《汉江韵》等。河南筝在演奏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右手的“游摇”,从靠近琴码的地方开始,流动地弹奏到靠近岳山的地方;同时,左手作大幅度的“揉颤”,音乐表现很富有戏剧性,也很有效果。河南筝的音阶特点,多用变徵而少用清角,近于三分损益律的七声古音阶,但二变音高,亦非绝对不变,往往会更高按到近于宫和徵。河南筝的曲调,歌唱性很强,旋律中四、五、六度的大跳很多,于清新流畅中见顿挫雄壮;频繁使用的大二、小三度的上、下滑音,特别适合中州铿锵抑扬的声调,充分体现地方方言特点,使筝曲具有朴实纯正的韵味。在演奏风格上,不管是慢板或是快板,亦无论曲情的欢快与哀伤,均不着意追求清丽淡雅、纤巧秀美的风格,而以浑厚淳朴见长,以深沉内在慷慨激昂为其特色。傅玄对河南筝曲的评价是“曲高和寡,妙技难工”。
山东筝:也称齐筝,多和山东琴书、民间音乐有直接联系,曲子多为宫调式,以八大板编组而成。其中一部分是作为琴书的前奏出现的琴曲,跟河南板头曲相似,有六十八板“大板曲”,如《汉宫秋月》、《四段锦》等。另外,也有由山东琴书的唱腔和曲牌演变而来的,如《凤翔歌》、《叠断桥》。演奏时,大指使用频繁,刚健有力,左手的吟揉按滑则刚柔并蓄,铿锵、深沉,其演奏风格纯朴古雅。
浙江筝:又称杭筝、武林筝,流行于浙江、江苏一带。代表作品有:《高山流水》、《将军令》、《四合如意》等。浙江筝以“弦索十三套曲”和“江南丝竹’、“杭州滩簧”为源,抒情性、戏剧性很强。在演奏风格上,一般节律都比较明快、流畅、秀丽。演奏特点有“大指摇”、“快四点”、“夹弹”、“提弦”等技法,并借鉴、学习、融汇了琵琶、三弦、扬琴乃至西洋乐器的演奏技法。
潮州筝:流传于广东潮州一带,以“潮州音乐”(包含丝竹乐、锣鼓乐、笛套乐、寺庙乐等)为基础。代表作品有:《柳青娘》、《寒鸦戏水》、《月儿高》、《锦上添花》等。最大特点是左手按滑音的变化,在潮州筝中,这一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到了十分绝妙的地步。实际上就是弹筝时通过左手按音的变化,以达到几种音阶和调式的组合形式,而且音律也不同于十二平均律和其他地方的民间音乐。潮洲筝以其右手的流畅华丽、左手按滑音的独特加花奏法,变化细腻、微妙而独具一格。潮州筝的主要曲调有“重六”、“轻六”、“活五”、“反线”等。其中“重六”调乐曲比较委婉,“轻六”调乐曲清新明快,“活五”调乐曲缠绵悲切,律调很有特点。
古筝大师曹正先生在其《筝艺春秋》中写到:“婴孩可以断奶,文化不能断乳。一个民族乃至个人,再没有比文化的断裂更令人揪心的!筝与文盲无缘,要摩挲文化,读历史学辩证法,优化学养,韧于躬耕知识园地。”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孤立地对待这朵传统艺术奇葩,应该将其融入到中华民族整个的文化洪流中传承和发展,如曹先生所言:“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容,大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