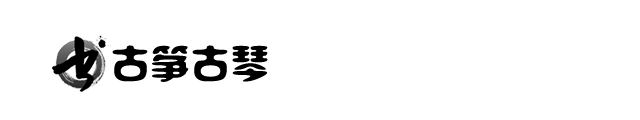chapter1:生而为音乐的天才少年,接受了音乐之神的第一次试炼 美籍华裔钢琴家安宁1976年生于北京,父母均出身于中央音乐学院。父亲安纯琪是钢琴家,师承作曲家吴祖强夫人郑丽琴女士。母亲是
大学期间,安宁在1997年刚过20岁时参加克利夫兰国际钢琴大赛并拿到了第三名。22岁时,安宁快要考硕士学位的时候,将要告别学校的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这种恐惧依旧来自疼痛和对未来的担心,因为担心,那时午夜梦回,安宁常常问自己:“难道我以后就要靠教四五岁的孩子弹琴为生吗?”而安宁这时期也有意无意地懈怠了练琴,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转行。
这时候,薛曼老师看出了安宁的焦虑,建议他去欧洲参加1999年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安宁答应参加比赛,但是并没有抱多大野心,他跟父母商量干脆借此机会来欧洲旅游,甚至做好了在第一轮就被淘汰的打算,准备带着父母去游欧洲了,没想到却收到了进入半决赛的通知。
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赛事,参赛人数众多,光是选拔赛参加的就有120多人,之后初选出来60人进行24席位的半决赛位置角逐。进入半决赛的安宁,由于事先根本未做打算,因此连第三轮比赛的曲目都没有背下来,就在比赛之前一天,练了11个小时,才把所有的比赛曲目背好。
在备战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最后两轮时,安宁每一轮都只有七天时间准备,选手们被封闭在一栋大宅子里,彼此都在独立的琴房练习,而且他们都只在被宣布入围时才能拿到比赛的曲目,要在七天时间背熟曲目,还要跟乐团完成合作。安宁感觉自己就快发疯了,拼命练,每天练八九个小时,练到七天当中的第三天时,他的两个肩膀又像着火了,而住他楼上的犹太选手已经学得很快了,这让安宁的心绪更乱,第四天安宁索性泡了一个热水澡,只练了一个半小时,他对自己说:“TRYYOURBEST!这个比赛花了我五个礼拜,已经数不清练习了多少个小时,不要想得失,只要尽全力就好。”
放下得失心为安宁带来了在决赛当中的超常发挥,像两年前在克利夫兰比赛一样,他这一次又拿了第三名,但是这个第三名可就不一样了,马上就为安宁带来了20多场音乐会的签约。更重要的是,从16岁开始受手痛折磨的安宁,在22岁参加这一次伊丽莎白比赛之后,就再也没有失掉对自己的信心。
“我很爱音乐,除了钢琴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它的事情想要做。可是,在参加伊丽莎白比赛之前,我真的很严肃地想过转行。我非常感谢这个比赛改变了我的生命。”安宁说。
1999年这次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之后,比利时的媒体就以“钢琴诗人”来称呼23岁的安宁。在安宁的22岁到23岁期间,他又经历了一帆风顺的日子。这一年,他相继获得美国钢琴家协会首奖、第六届美国国际肖邦钢琴大赛首奖、美国哈佛音乐协会ArthurFoote奖和美国PresserFoundation奖。
随后,在2000年,安宁获邀参加美国盐湖城的GinaBachauer国际钢琴音乐节,举办独奏会,会后全场观众起立欢呼,并得到音乐评论家JeffManookian极高的评价:“他的但丁奏鸣曲有独到之处,这首技术上极为复杂的曲子,在他的巧手下成了一首感情丰富的诗,在安宁一阵阵排山倒海的乐音下,把李斯特对于但丁罗曼蒂克感情的诠释,在舞台上完全释放出来。”
参加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不仅为安宁带来了演出机会、带来了自信,更重要的是,让他被一双同样来自东方的眼睛关注在这一届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的评审当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钢琴大师傅聪。安宁正是通过这个比赛认识了傅聪,当时的傅聪评价安宁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富有内涵的钢琴家演奏了”。
比赛结束后,傅聪邀请安宁去喝茶,大师说,他从安宁的琴声当中听出了中国文化,感到他乡遇到了知音,于是边喝茶边给安宁念了很多诗,安宁还很清晰地记得那是王维的诗。之后,傅聪便邀请安宁前往英国,在自己的家中为安宁上了大约一个星期的课。
在傅聪的英国家中时,安宁每天清晨开始练琴,练至中午,下午傅聪练琴,两人一起晚餐后再上课。除了练琴之外,他们谈了很多很多,往往是傅聪抛出一个中国古典的诗或者画,而安宁就以西方文化来做答,两人在一应一答之间,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艺术,一老一少两位钢琴顽童就这样天马行空地任由音乐与思想穿梭东西、纵游古今。
傅聪常常用父亲的教诲来自勉:“从事任何艺术,最重要的是永保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即是纯净、纯真地向往艺术的心灵,傅聪与安宁这一老一少因钢琴结缘,正是缘于两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2000年10月,安宁作为第六届美国国际肖邦钢琴大赛的冠军,前往波兰华沙参加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跟安宁同样参加这一届比赛的,有年仅18岁的李云迪和他的师姐陈萨。后来已经众所周知的是,在这一次比赛中,李云迪拿下了冠军,从此成为第一位摘得这个世界上最著名、最严格、最权威、历史最悠久、级别最高的钢琴比赛冠军的中国人,陈萨拿到了第四名。而安宁,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被挡在了决赛门外。
前往华沙之前,安宁没有想到,音乐之神在刚刚对自己展开笑容的时候,再一次将他推向试炼的火焰。2000年,24岁的安宁通过一系列比赛的骄人成绩,尤其是美国肖邦大赛的冠军这一头衔,使得他在华沙一亮相就成为了焦点人物。同样表现出色的李云迪,与安宁一起,被华沙当地媒体预测为最有冠军相的两个人,认为第一名无疑将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
当时带着李云迪和陈萨前往华沙参加比赛的深圳艺术学校教授但昭义,也早就认识安宁,但教授鼓励李云迪多跟安宁聊聊天,于是安宁和李云迪两人就在华沙的肯德基里边吃汉堡边聊钢琴,也没因为两人是竞争对手而互相心存芥蒂。
在来华沙之前,安宁颇有志在必得的来意。因为在夺得美国肖邦大赛冠军之后,安宁就一直在按照大赛对冠军的规定,展开了多场巡演,而且曲目全都是肖邦,可以说准备得比以往任何一场比赛都充分,练习时间都更久。为了华沙肖邦比赛,安宁准备了一首自己此前从未演奏过的回旋曲,而这首回旋曲也被当地媒体引为经典,因此安宁顺利地把比赛的第二轮、第三轮弹完,表现非常稳定,都没有出什么纰漏,他也就安心地等待评审团宣布决赛入围名单。
让安宁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没有在决赛名单上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听错了,再三确认之后,安宁知道自己的确不在决赛名单中,于是向大赛艺术总监阿格丽希询问究竟,阿格丽希作为比赛艺术总监的权限是监督评审团的运作,但并不拥有投票权利,因此阿格丽希保持了旁观的清醒和公正。阿格丽希告诉安宁:“你本来已经进入决赛的八人名单了,但评审团临时决定把决赛名额减为六人,因此进行了第二轮投票,你很不幸地在第二轮投票时和另一位罗马尼亚的女选手一同被淘汰掉了。”
大热倒灶,安宁居然没有进决赛的消息,也震惊了华沙当地媒体,报章纷纷发表文章质疑半决赛的公正度,但媒体的呼吁也改变不了大赛已经既成的现实。备受打击的安宁感觉非常冤枉,不愿意继续多待一分钟了,他不等决赛开始就离开华沙回到美国,连评审团在决赛之后颁发给他的评审团特别奖“AlfredCortot奖”都没有去领。
由于2000年这一届赛果的争议太大,因此五年一届的波兰华沙肖邦大赛从安宁参加的第二届开始更改赛制,从2005年起该比赛有了一条“安宁规则”。在台湾作家焦元溥所作的《游艺黑白》一书当中,来自越南的钢琴家邓泰山接受采访时透露了华沙肖邦大赛的“安宁规则”的由来。
邓泰山是2005年华沙肖邦大赛的评审,他曾经于1980年获得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也是第一位在该赛事当中夺冠的亚洲人。邓泰山担任评委的2005年这一届肖邦大赛改变了赛制,“首先,取消了录影带甄选,改成在比赛前一周进行初选,这个初选在华沙举行,但评审都是波兰音乐家,初选大约选80位钢琴家进入正式比赛。第二,正式比赛从四轮改为三轮。第三,决赛原本只有6个名额,改为10个名额。而发生这样的改变,就是因为2000年那一届比赛的争议太大了”,邓泰山说:“我上次去华沙,大家都在谈论安宁,说他演奏是多么杰出,大家对比赛结果也都很有意见。初选和正式比赛分开,好让一些没能力的人淘汰出局,把正式比赛给真正有实力的选手。而决赛增加名额,我想总能比较能避免像安宁这样的好手被恶意挡在决赛门外,导致决赛乏善可陈,让一些缺乏实力的人得奖。一旦真正的好手进了决赛,决赛也就是公开的竞争,好坏大家都看的到,舆论压力也会更大。”有趣的是,邓泰山以及波兰华沙肖邦大赛的评审们从此以后都将这一条决赛规则叫做“NingAnrule”,即“安宁RULE”。
安宁被恶意阻挡在决赛门外的事件,不单是直接导致波兰华沙肖邦大赛有了“安宁RULE”,也让更多的音乐界专业公司、乐团向安宁伸出了橄榄枝。比赛结束不久之后,大赛破例为安宁这个落选决赛的选手出版了比赛曲目的CD,而此前出版CD的选手都是第一名。随后,华沙交响乐团邀请安宁在庆祝该团成立一百周年音乐会中演出肖邦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而这一首曲目正是安宁没有机会在决赛中演奏的曲目,在2002年1月底安宁再次受到华沙交响乐团的邀请,与该团于美国巡回演出肖邦钢琴协奏曲。
这些来自音乐界的声援,都让安宁原本因为这一次打击而倍感失落的情绪,得到了安慰,很快重新振作起来,相继于2002年夺得美国Rachmaninoff国际钢琴大赛“最受观众欢迎奖”、2003年美国WilliamKapell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2006年丹麦Tivoli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这期间,安宁在台湾出版了“火热与冷静之间”专辑,获得了2005年台湾金曲奖最佳古典演奏、专辑双料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