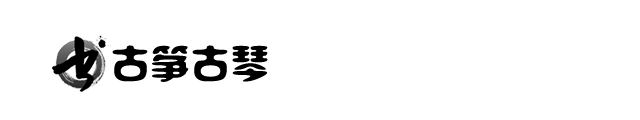在钢琴演奏家印芝看来,印象派艺术的美感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具有一种“开放性”,正如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记忆,往往不是起承转合、逻辑完满的线性叙事,而总是飘然而来、倏忽即逝,如万花筒般绚烂的“碎片”印象。印象派艺术作品不断变化的姿态、若隐若现的线条、转瞬即逝的灵感,也需要敏感和富于想象力的心灵去捕捉、感悟、延展、填充。
1874年,法国画家莫奈的《印象·日出》使得一种全新的美术创作潮流被冠以了“印象派”的名号。这一潮流中的著名画家还包括雷诺阿、毕沙罗、塞尚等人,他们在绘画作品中捕捉光影的变化、突显色调的差异,被描画的事物主体好像第一次成为配角,而赋予它色彩的光线才是艺术家真正关注的焦点。自此,西方绘画纤毫毕现的高度写实追求在朦胧的笔触面前化为了模糊的轮廓和斑斓的色块。
同样在十九世纪的尾声,来自法国的作曲家德彪西在音乐中实现了“印象派”的艺术效果,巴洛克时期缜密繁复的声部对位、古典主义时期平衡清晰的章法结构、浪漫主义时期奔放肆意的恢弘音响,以一种奇妙而轻柔的方式实现了融合与超越。无论是钢琴独白还是交响诗篇,德彪西似乎让音乐第一次失去了“重量”,成为漂浮在空气中的瞬间情思。而比他年轻13岁的法国同胞拉威尔同样被视作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人物,后者以更为细密的笔触和宽广的视野书写下那些如珍珠般剔透的音符,令众多音乐同行发出由衷的赞叹。尽管德彪西和拉威尔本人都对所谓“印象派作曲家”的称号持保留态度,他们的音乐写作与法国音乐传统、象征主义文学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多民族文化交融有着同样密切的关联,但那份浸润在音乐中的朦胧之梦与诗意之境,的确带给听者无限遐思。
值得一提的是,德彪西和拉威尔这两位法国作曲家都曾经写下过精湛卓越的西班牙风格作品,以一座比利牛斯山与欧洲大陆相隔的西班牙,也的确与法国的艺术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和频繁的互动。这就不难解释为何阿尔贝尼兹和格拉纳多斯这两位十九世纪末最为杰出的西班牙作曲家、钢琴家都曾前往巴黎长时间深造学习,还写出了众多同样具有印象派风格的音乐佳作了。
印芝将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德彪西、拉威尔、阿尔贝尼兹和格拉纳多斯,视为一座华美雕塑的四个侧面,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对比观照下的交相辉映是一种极为奇妙的体验。在她所师承的俄国钢琴学派中,让颗粒性的音符连缀成真正的乐句,让钢琴实现自由的歌唱,是最核心的艺术追求。这一次,她将用琴声带领听众穿越回一个世纪前的梦幻花都,在黑白琴键上弹奏出五彩音符。
音乐会的上半场,听众将在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细密笔触下邂逅鲍罗丁与夏布里埃这两位音乐史上的巨擘;在《镜子》组曲的光影折射间观览“海上孤舟”,在德彪西动人的“月光”光晕下踏上前往“欢乐岛”的旅途。下半场,心随境转,听众将在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兹的笔下赏析欧洲视角下独特的东方韵味,在格拉纳多斯的音律中聆听《戈雅之画》的纯真细腻、极致浪漫。
4. 剧院会员电话预定门票最多保留一周(最低价位不可预定),逾期将被系统自动解除锁定,演出开演前7天不接受预定。